这是王言民先生的遗稿,写于三十年前。幸冯作明先生保留有手写原稿,分享与我,方得与读者见面。王言民先生是作家、诗人,也是书法家,遗憾英年早逝。今读旧作,如晤其人。恍见列位博山艺术大家朱一圭、王延山、蒋正和、胡升刚等,在高峡平湖把酒临风,宠辱偕忘,其喜洋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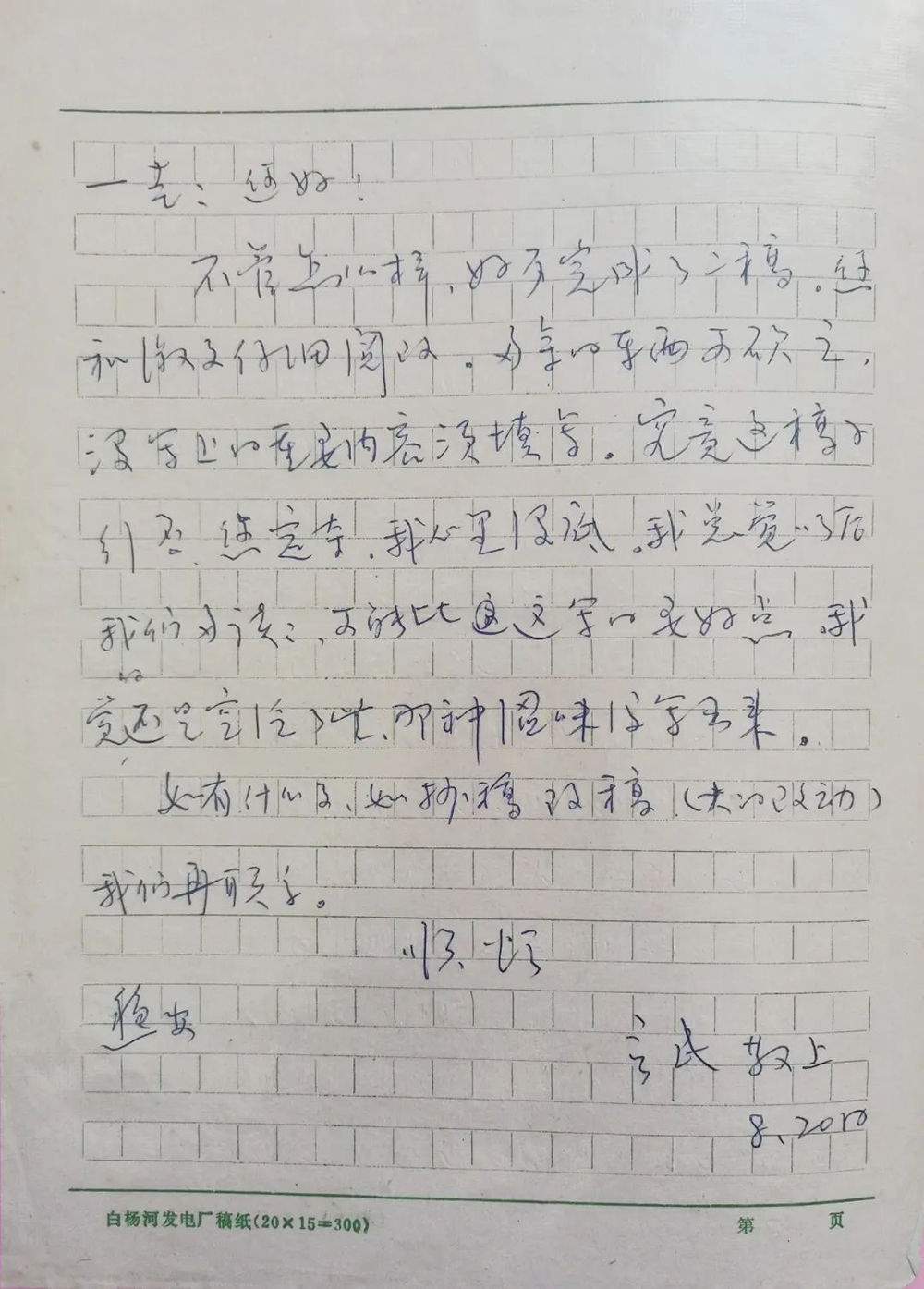
一
近几年,朱一圭和所有出了名的人一样,各种荣誉和头衔接踵而至。镁光灯盯着他的那张坚毅的脸,闪个不停,然后连他的形象一起连篇累牍地见诸于报端和刊物。应当说,所有的那些赞誉并不过分,过分的倒是他本人,他总是躲开那些喧闹的地方,仍旧和过去那样默默地生活着,工作着,置各种名誉于度外。这一点,熟知他的为人的人,仍然感到他依旧是原来的那个人,依旧简装布衣,依旧是木讷而沉稳的样子。你要与他谈话聊天,仍旧是那副永远思索着什么的神情。
如今,朱一圭可不再是微不足道的陶瓷艺人了,他已经功成名就,是淄博美术陶瓷厂的总工艺美术设计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淄博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博山区政协副主席,成了现代画坛公认的陶瓷艺术家……这一切绝然不是生活对他格外的恩赐,而是以他顽强的追求和奋斗换来的。然而,他仍把这一切看作虚名,他认为,重要的还是他的艺术。他懂得什么叫永恒,因此在觥筹交错的酒席上,在一般的会议桌上,要找到他太难了,他的身影几乎永远贴在工作台上。
我们走近他,他很热情,总是那么真诚,但他永远不放弃思索的权利,善于思索,捕捉灵感,成了朱一圭的第二天性,思索孕育,是他的积累,他会突然像触电一样,在黑夜中让人瞬间能看到山川河流和季风摇曳的树影,使你的心灵不再感到孤独,感到大自然和生活的美好。
朱一圭是一个不知疲倦、不断思索的艺术家,总是充满了创作欲望和炽热的激情。
二
身份和地位的改变,使朱一圭更加谦逊和朴实了。到他住家找他,那是必得有向导才行。到朱一圭家,要经过一条非常狭窄的小胡同,窄到两人碰面时,必须要礼让一下才能过得去。然后是一个大杂院里那18平方米的古老的青瓦平房,屋里拥挤得几乎没有插足之地,你绝不相信屋里的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登上艺术殿堂的艺术家,惊愕之余,面对主人,你立即感觉到你走进了一个非常深邃的历史通道,这里足以震撼人的灵魂。它会吸引你向纵深处穿越。你将慢慢从他丰富的精神内涵里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朱一圭的艺术生涯,是一部含泪的生命史。他的每一步深深印着生活的艰辛,他在登上艺术殿堂、端坐在某个辉煌位置的时候,罩在他头上的光环,都是用眼泪和汗水灌注的,即使这样,你平时也听不到朱一圭抱怨命运的只言片语。像默默接受荣誉一样,朱一圭也默默承担了一切磨难和不幸。
不幸和磨难,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叩他的命运之门,11岁,他单薄而脆弱的心灵就被丧父之痛击碎,家庭支柱倒了,顷刻,一切生活的重荷压在他稚嫩的肩上,像山洪爆发摧毁堤坝一样,摧毁了他天真而幸福的童梦。为生存计,为了母亲和幼弟,他到烤花作坊里画碗,开始走上漫长而艰辛的生活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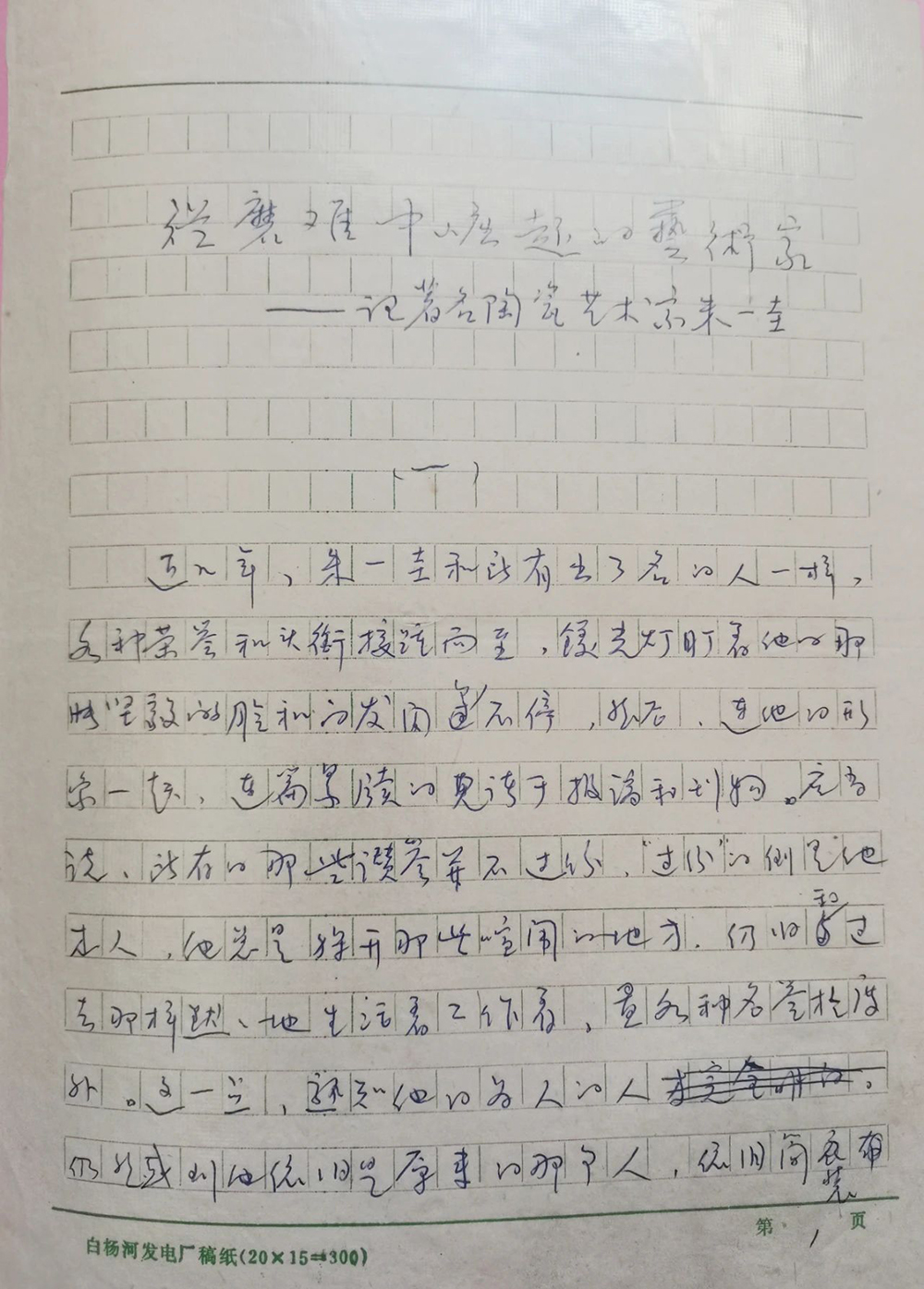
画窑货挣钱糊口的人,在山头镇,何止成千上万,这种劳动又苦又累,单调而机械,几代人,画了一代又一代,直到画驼了背,也还是那几个一成不变的老样子,什么“太师少保”“花有清香”之类,对别人来说,熟到闭上眼睛也能一笔不走样地画出来,并且以此沾沾自喜,津津乐道,而朱一圭,他早已从这里边体味到了一种被庸俗俘掠与同化的危险。从童年时代就对绘画艺术的爱,现在又萌动了一个新的渴求。当一辈子画匠是最没有意思的事了。他机敏的触须开始了寻找。
三
使他有幸免于在窑货堆里湮灭灵性的,除了他自身的素质外,是他的表兄路大荒和一位有眼力的女画师张淑贤。他们从眉宇间发现了朱一圭的一种闪光的潜质。路大荒对他说:“你还是在家乡做一个土生土长的画家吧。”
于是,他如饥似渴地学起绘画来。女画师一边教她学问,一边教她画画。这种启蒙教育,对朱一圭来说,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非常幸运的。就像一个出远门的人,手里必须加一把伞一样,一旦下起雨来,可免遭雨打,他同样用手中的画笔,把俗气和平庸抵挡住了。俗气和平庸这种极具侵蚀力的东西,简直像病菌一样,一旦染上它,就成为难以治愈的痼疾,在艺术长河里,多少有才华的人难逃这种随俗从流的厄运。朱一圭的起点就在一个正确的跑道上。
于是他拼起命来了。朱一圭常说:“认定一个目标,你就应当毫不姑息自己的一切去争取达到。”他涉猎的范围很广泛,国画,书法,雕刻,制砚,并且潜心研读古今中外名著,他从古代文化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从俄罗斯文学里学到了深厚与质朴,从西欧文学里学到了博大与精深。他欣赏到列维坦的抒情诗人的气质,赞叹毕加索的破坏的勇气,从莫奈、梵高里,懂得了也品尝了艺术变革的那种老辣的涩味。这一切,使他具备了一种狮子般吼叫的勇气,也具备了老黄牛的无限的韧性。他已经有了向平庸挑战的能力,执在手上的画笔,已经可以向一个崭新领域,向一种高层次展示一个艺术家心灵的悸动了。
这种苦行僧式的刻苦的生活,使他产生了某种飞跃,也使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时,病魔受死神的差遣,又一次叩响他的命运之门。多年来,经常从深夜熬到黎明,白天又要坚持上班,街坊邻居整天见不到他的影子,忘记了他的存在,不知从何时起,他开始咳嗽,把一汪汪鲜血吐到墨染的宣纸上。起初他根本不当回事,后来越来越厉害,脸一天比一天蜡黄消瘦。在别人的催促下,他才到医院里,医生告诉他,必须动手术,你的肺部有肿瘤。20岁的生命被病魔横挡在了美好憧憬的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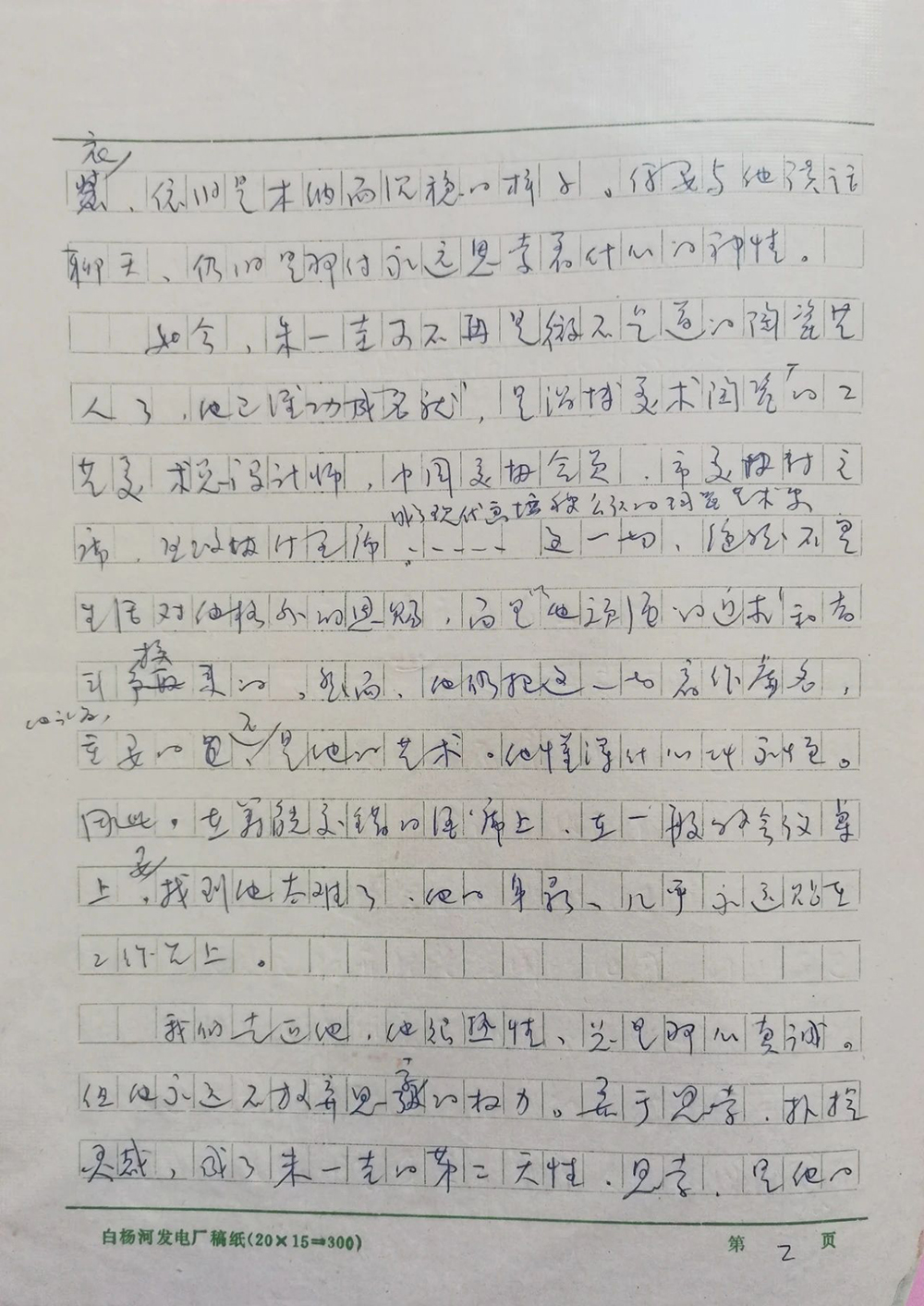
熊淑文,一位让人崇敬的女性走进了朱一圭的生活,她有着诗人的气质和画家的才能,她不顾世俗偏见,深深地爱上了朱一圭。
她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始终如一地安慰关心他。朱一圭读过但丁的《神曲》,面对地狱,他平静地对她说我是去死的,你应当有你自己的生活。朱一圭面对死亡的威胁,表现了非凡的勇气,在他看来来到这个世界和告别这个世界是一样的自然,只是,丢下了艺术,他才真正感到痛苦和遗憾。
女朋友的爱和她顽强的毅力,使他战胜了死神,命运向他露出了微笑。出院时,他回到他的幽暗的画室,发现墙壁上悬挂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女朋友知道一个从死亡边缘上活下来的人,看到这种永恒的微笑,心里会生出宽慰与激情。
四
契科夫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平民阶层的作家登上艺术高峰,要比贵族阶层的作家付出大得多的代价才能达到,对艺术家来说,还有什么比庸俗更可怕的东西呢?艺术和在生活底层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来说,几乎是两极的距离。朱一圭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像其他人一样,不断受到生活种种的诱惑,这些诱惑像无数只手向平庸乏味的泥淖里拉他,对他来说,只有一步之遥,他即可陷进去,万劫不复。但是朱一圭选择的是探索一条漫长跋涉的艺术新路,他要赋这些黑色的陶土以新的色彩和新的生命。
在博山这个陶乡里,流行着一句俗语:人一辈子谁不打个黑碗?这里除了有另一种含义外,还说明了黑碗的极不值钱。朱一圭就是从这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黑陶里,找到了能释放他才能的艺术天地,使他的才华在1300度的窑温中,一次次接受冶炼。
这里有一个记录,可以使人既吃惊又不得不敬佩朱一圭的顽强精神。在立粉彩陶这个陶瓷史上突破性的试验中,几乎达到了近千次,每一次失败都像烧红了的烙铁一样灼伤他的心灵,每一次失败在孕育成功的同时也产生绝望。失败带来的心理障碍,甚至比冷嘲热讽更难跨越。当他终于听到实验成功的消息时,他平静地坐在那里,没有运动员打破世界纪录时的那种激动心情,盈在眼眶里的两滴清泪,始终晶莹久久地在闪烁,这里喜悦已经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人格的完美与升华。他的挂盘在国际展览中标出高价即刻告罄,而他的人格呢,却是无价的。
1979年2月,他的代表作《竹鸡》被选为国礼,随邓小平出访美国,飞到大洋彼岸,赠送给了美国的参众两院。这件有意义的作品成了这次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内容。镁光灯射下了这伟大的一瞬。
五
立粉彩陶的实验成功,他的妻子比他更激动,甚至是心酸。不堪回首的往事,却在这时刻挥也挥不去。磨难是朱一圭生命的一个很长的环节。“文革”期间是最突出最惨重的一环。
突如其来的灾难,使他一夜间变成了反革命分子、反动技术权威,在劫难逃的厄运一下子就掳去了他12年的宝贵光阴。监督劳动清扫垃圾代替了有灵性的艺术创作,失望孤独制成了一张透不过气来的巨网,无端的冤屈,无法排遣的痛苦,不断地折磨着他,他的人的尊严,他的神圣的艺术,被无情的海洋吞没,化为灰烬,他的工作室,他的刚刚植被茂盛的绿色的艺苑,顷刻间成为一片焦土,朱一圭在这片废墟上站成了一尊雕像,苦苦思索着俯身捡拾的是思维的碎片,这是他唯一未被剥夺的权利。他要重新凝铸他的艺术观,完成他的弘扬民族文化的宏愿。
那时,没有人敢接近他了,他每天早晨要比别人更早地徒步走十华里路,赶到厂里打扫卫生。书包里装的是煎饼,咸菜,生活拮据得几个月不见荤腥。每天他遭遇的是蔑视的眼光,无休止的批判,必须承认的莫须有,否则,将课以更严厉的惩罚。磨难当中有磨难,年逾古稀母亲以及岳父母三个老人相继瘫倒在床,女儿、儿子还小,不谙世事,在学校受到别人的凌辱,回家来哭鼻子。苦难的极限便是麻木。朱一圭一边蒙受屈辱,一边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当孝子,做好女婿,好丈夫,好爸爸。他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站在院子里,仰天发出浩歌长叹呼唤力量。维系朱一圭的生命之弦,几乎随时都有崩断的危险,而信念之舟也面临捲沉的厄运。

在这险恶的环境,在这多灾多难的生活里,他妻子与他患难与共。她妻子也是画家,她有她辉煌的才能,但是她却知道自己的责任,总不能两个人一起毁了他,把自己的才能小心翼翼地掩藏在心灵深处,把大部分的家务活揽过来,让朱一圭遇到的永远是安宁和温馨的目光,这目光犹如无风无浪的港湾,使朱一圭受伤的心灵得到宽慰和暂时的安歇。她把一切烦恼都挡在18平方米的外面,挡在她爱心所能波及到的遥远海域之外,朱一圭在这里获得重新能活下去的勇气。
几年来,常常是利用中午一个多小时吃饭的时间,不管是风霜雪雨,熊叔文骑车匆匆赶回家,照料好三位老人,婆婆、母亲病重完全不能自理,她要给她们先后换下尿布,以最快的速度做好饭,恭恭敬敬地端在他们面前,还要照料孩子,常常自己来不及吃饭,就急急忙忙地回厂上班。晚上回家来一直熬到深夜,洗好又臭又脏的尿布,料理好一切杂活,然后自己才休息几个小时。那时她像一个上足发条的机器人,几年里,把自己熬成了一颗瘦挺挺的高粱杆。流了多少泪,做了多少噩梦,只有枕头知道。一到人面前,她安详平静到像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永远微笑,坚强得不向任何人诉苦。母亲看着他心疼,只想找个头去死,来减轻她的负担,这一切她都默默承受下来,只是为了让朱一圭在饱经忧患、尝尽世态炎凉的人间不幸里面,也能进入一种完全的充满活力的艺术想象中,心灵不被封冻,艺术清流不被污染。
六
朱一圭在这片黑土里长成了一冠树,葱郁的大树,每片树叶在阳光下摇曳着炫目的光芒,这棵树拔地而起,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向人们展示了艺术和艺术家的风采。
朱一圭的立粉彩陶挂盘发展了花斑釉的绚丽多彩的特长,通过高温窑变使大黄,粉蓝,铜绿,玫红等几十种颜色大放异彩,加上新颖别致的构图,成了人人喜爱的艺术珍品,把它称作魔幻艺术,国内外艺术家对他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自己成了画坛上名闻遐迩的陶瓷艺术家。
他的作品是他生命的心灵的歌,显示了朱一圭多彩多姿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在这里,色彩与结构已经不再板滞,而是灵动,不再是单一,而是多层次,充分显示了朱一圭的创作才能。他所使用的绘画语言,既是民族的,同时也融进了西方的现代意识,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是我国陶瓷艺术宝库里一颗耀眼夺目的珍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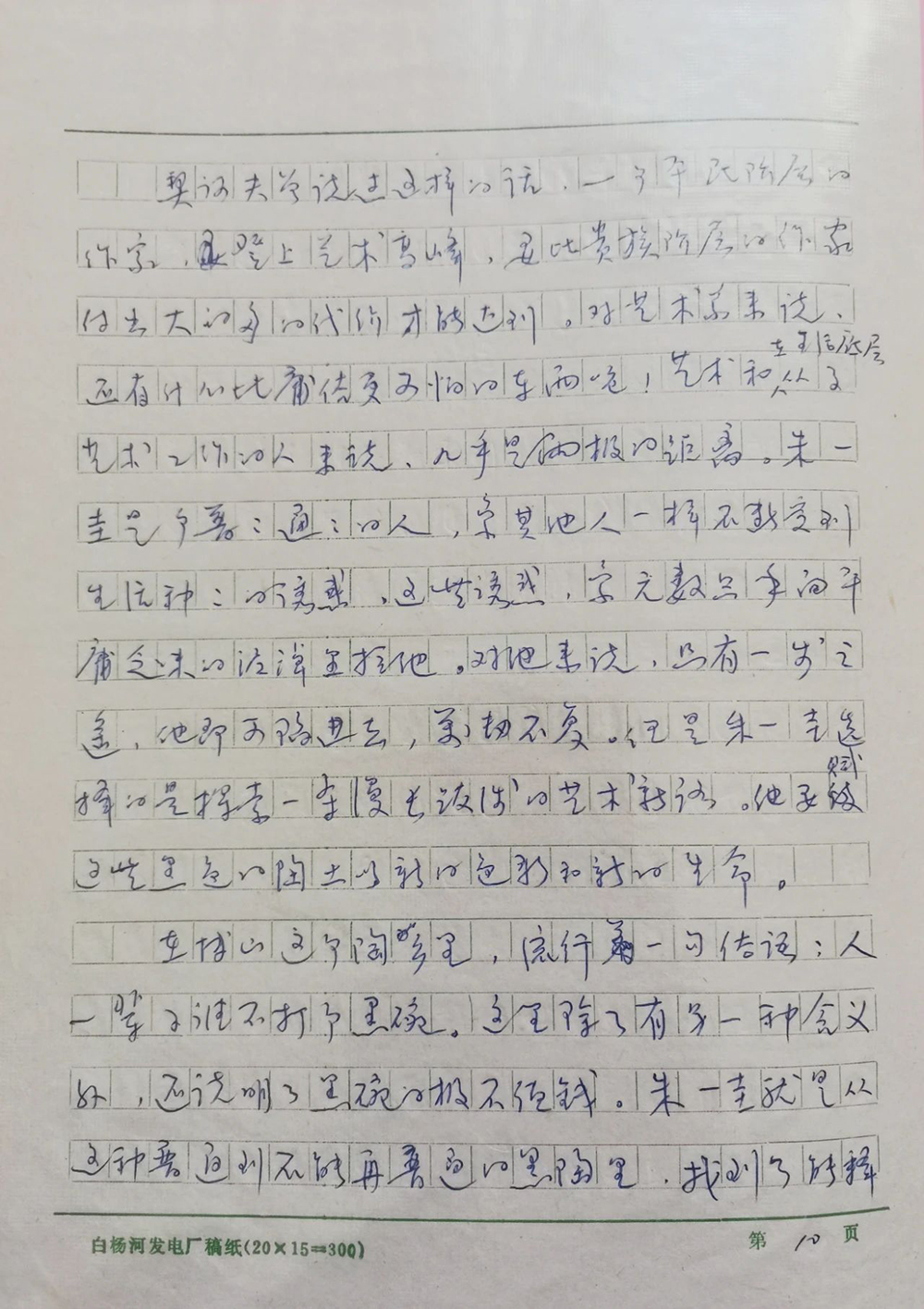
朱一圭的艺术成就使他在艺术界有了许多知音,许多朋友,有画坛仅存的耆宿,也有名不见经传的画坛新秀。他们从北京,天津,上海,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山头小镇,吴作人,黄胄,侯一民,范曾,吴冠中等等,名字可以列一大串,他们带着好奇求知,想欣赏这位点石成金的独辟蹊径的艺术家,怎样作画,怎样生活,他们很快就找到这位艺术家的闪光点,发出由衷的赞叹。
著名歌唱家吴雁泽,今年夏天新婚燕尔后到故乡来,专门拜访了朱一圭,他们在艺术探索上有相似之处。吴雁泽在融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上开创了声乐界先河。朱一圭在继承中国画的传统上,同时也吸取了西洋绘画的技巧。我们在欣赏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当中,为什么都同时感受到艺术的魅力,感受到了一种穿透灵魂的力量,他们在掌握音乐语言和绘画语言的技巧上有高度的和谐性、统一性,足可以和世界上任何高层次的艺术对话,因此,在国内外都享有崇高的荣誉,成为淄博人的骄傲。
朱一圭是位有个性的艺术家,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他不落前人窠臼,不断啄破束缚自己的外壳,孵化出新意。他的沉潜的创作风度,他的远见卓识不断促使他往前走去,近年来,他又把立粉彩陶的技艺开辟了壁画这个新的领域,在全国许多大城市的高楼大厦的墙壁上,高悬着他的立意新颖、雄浑中透着灵秀的壁画,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他的小壁饰在美国卖出了极高的价钱,在国际国内市场上越来越走俏。
七
著名画家范曾到淄博美术陶瓷厂参观访问。他站在朱一圭作品面前,久久凝视不动。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朱一圭的经历和他在艺术方面所达到的境界,深深感动了他。他挥毫写下一首诗,“千锤百炼艺为囚,苦恨艰难五十秋,一圭生涯本是土,无穷智慧冠同俦。”高度赞扬朱一圭的艺术。这些年,他虽然有了名望,有了地位,仍然淡泊名利,仍然甘心囚在艺术事业里。不要说别的,光是副厂长这个头衔要一套宽敞舒适的单元楼,根本不成问题。厂里领导照顾他,一次次催促他搬到厂区宿舍,这里有诸多方便,但他还是拒绝了。他深怕日常生活的应酬,破坏了一种极为珍贵的艺术氛围。那一年,他以省劳模的身份到太阳岛疗养大自然的美,生活的舒适恬静,并没有让他陶醉,只是在疗养院圣地待了一半时间,他便匆匆赶回厂。“我是土命,我的生命离不开黑陶。”
还是那18平方米的老住屋,老住屋的简陋和陈旧掩盖不了这位历经磨难的艺术家的光辉。他每天仍旧骑车来回赶班,路上碰到他,他会向你微微一笑,如果你细心就会观察到,岁月在他的两鬓和额头上留下了痕迹,而他仍是那个样子,脸上充满了刚毅,仍旧是在永远思索着什么的神情。(王言民)
1992年8月20日
来源:颜山孝水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