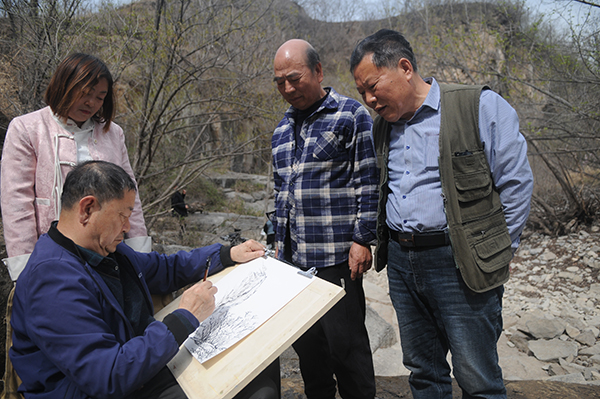晚清末造,文人士夫鉴藏并研究金石古物蔚为一时风气。据《天咫偶闻》说:“方光绪初元,京师士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尚,竞扬搉翁大兴、阮仪征之余绪。当时以潘文勤公、翁常熟为一代龙门,而以盛、王二君为之厨顾。四方豪俊,上计春明,无不首诣之,即京师人士谈艺,下逮贾竖平准,亦无不以诸君为归宿。厂肆所售金石、书画、古铜瓷玉、古钱、古陶器,下至零星砖甓,无不腾价蜚声,而士夫学业,亦不出考据、赏鉴二家外。未几,盛司成有太学重刊石鼓文之举;未几,王司成有重开四库馆之请,盖骎骎乎承平盛事矣。”民国以降,此风非但没有消歇,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品鉴金石古物的社团如雨后春笋,金石类报刊也层出不穷。
鉴藏研究金石古物离不开拓片,拓片的存在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整纸拓单片,另一种是剪裱本,便于携带。晚清民初,摄影术和新型印刷机械的传入,为金石拓片的复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金石拓片的剪裱本,不仅便于印刷,而且便于携带,所以被大量复制。与之相较,整纸拓单片复制品就少得多。
整纸拓能够帮助观者了解金石器物的原貌和全貌,对金石学者而言更为重要。兹就营业书目所载资料对晚清民国的金石整纸拓单片复制品略加稽考。
金石整纸拓单片复制品溯源
晚清同光年间,金石学家陈介祺就曾以木刻、照相、石印等多种方法复制金石整纸拓单片。
据史树青、傅大卣说陈介祺“所藏西周毛公鼎全形拓本及铭文,除少数是原拓外,多数是刻在木板上拓印,木板所刻铭文拓本,后人往往认为拓本是真器原拓。毛公鼎铭文以分成四段为原拓,因此,据拓本所刻的铭文与原拓失误多处。近几年,有些国内外研究金文的学者,误认为毛公鼎有两件,甚至怀疑毛公鼎原器为伪者,皆受陈氏木刻拓本影响所致。”

木刻之外,陈介祺还尝试过照相与石印。
在光绪元年正月廿六日,陈介祺致书吴大澂,说:“兹有表弟谭雨颿名相绅,旧在潘世兄霨署中习得西人照法,以其法形似而不大雅,故不取。后见其照山水树木得迎面法,于凡画稿皆有神,照碑帖则近雅而未甚古也。今试令照三代文字拓及器量图,乃至佳,虽缩小而能不失其真,且似字之在范经铸者,浑朴自然,字虽小而难刻,然上海刻工或能之。器外象形文虽不能甚晰,有拓本相较,亦易审。有一图及图拓,虽不见器亦可成书,且可将难得之拓印传之,是法乃为有益于中国艺文之事矣。……且望照各吉金与唐宋拓秦汉石,与人间难得本也。(周聃簋拓一纸、说一册、钱款识读记一册、缩照吉金图五、款四、印一、石印拓五、乞察入)。”信中所言“缩照吉金图”就是照相复制品,“石印拓”则应为石印复制品。
制作金石整纸拓单片复制品,陈介祺还不是最早的。正如吴云在给陈介祺的一通复信中所说:“承示用洋法缩照彝器及书画各图,此事南中已数见不鲜。”
至迟在同治初年,在上海,就有人以照相术和珂罗版复制书画字帖等古物。据王韬说:“西人照像之法……一照即可留影于玻璃,久不脱落。精于术者,不独眉目分晰,即纤悉之处,无不毕现。更能仿照书画,字迹逼真,宛成缩本。近时能于玻璃移于纸上,印千百幅,悉从此取给。新法又能以玻璃作印板,用墨拓出,无殊印书。其便捷之法,殆无以复加。”葛元煦亦云:“以此法(照相术)照各种字帖,收缩较蝇头尤小,将显微镜观之,丝毫不差。”
对清季“传古之术”做过专题研究的李军也指出:“在南方如广东、上海、苏州等地,利用照相技术,拍摄金石拓片,力求传真,并非自陈介祺开始,以吴嘉善、邹伯奇等熟知西学之人为代表,早已进行过尝试。”
营业书目里的金石整纸拓复制品
营业书目是书店等出版机构为出售图书而编制的小册子或单张的供招贴的传单。也就是说,营业书目是销售图书的书目广告。
金石整纸拓单片复制品不同于成册的碑帖或画册,它们是在单叶纸上刷印出金石拓片的全貌。在营业书目中,它们有着不同的归类。艺苑真赏社的营业书目中叫“金石单片”,其他出版机构的营业书目则归在“堂幅屏条”类或“屏联堂幅”类。
笔者搜讨经年,得民国艺术类营业书目卅余种,今将其中所见金石整纸拓单片复制品胪列如下。
(一)艺苑真赏社1921年印制的《金石书画目录》列有“金石单片十种”,仅给出了价格。
1、周盂鼎铭,四角。
2、周毛公鼎铭,五角。
3、周散氏盘铭,四角。
4、周虢季子盘铭,四角。
5、周秦二罍铭,四角。
6、秦泰山二十九字,八角。(据王壮弘说为严可均藏本)
7、秦琅琊台刻石缩本,四角。(据王壮弘说为阮元旧藏,有翁方纲题字。)
8、西汉杨量买山记,五角。(上有赵之谦题字,据王壮弘说此为重刻本。)
9、吴天发神谶碑缩本,四角。
10、隋陶贵墓志,四角。
(二)西泠印社1927年印行的《西泠印社书目(第二十五期)》里有“玻璃版印堂幅屏条”类,列出金石拓片复制品四种。为毛公鼎全形拓本(有孙仲容、徐籀庄、吴清卿释文,诸名家题跋)、盂鼎铭拓本挂屏(考据精碻,名家题跋甚多)、曶鼎铭拓片挂屏(有诸家考释,题跋甚夥)、散盘铭拓本挂屏(有数十家名人题识及释文)。在西泠印社1935年印行的《西泠印社书店书目》里,对这些金石整纸拓单片复制品的用纸、印制方式、尺寸、价格都有详细的说明,并配有珂罗版图样。


1、毛公鼎拓本立轴,分两张,第一张是铭文拓本,第二张是全形拓本,皆题跋累累。连史纸石版精印,长市尺四尺,阔二尺,定价洋三元二角,寄费洋一角一分。
2、散氏盘拓本立轴,名家题跋累累。罗地纸玻璃版精印装裱一轴,长市尺六尺,阔一尺六寸五分,定价洋二元四角(裱工在内),寄费洋一角三分。
3、盂鼎拓本立轴,名家题跋累累。罗地纸玻璃版精印装裱一轴,长市尺五尺三寸,阔一尺七寸,定价洋二元四角(裱工在内),寄费洋一角三分。
4、曶鼎拓本立轴,名家题跋累累。罗地纸玻璃版精印装裱一轴,长市尺五尺三寸,阔一尺七寸,定价洋二元四角(裱工在内),寄费洋一角三分。
(三)中华书局1931年印制的《中华书局重版名人书画屏联堂幅》中有“吴大澂秦汉砖瓦文屏”,所印的应该是吴大澂收藏的秦汉文字瓦当和文字砖的拓片,仅给出了用纸和价格。
吴大澂秦汉砖瓦文屏,是一套六条屏。单片,每堂六条仿古一元二角、六吉九角。裱工外加,平裱每堂六条一元八角。
“仿古”指的是仿古宣纸,“六吉”指的是汪六吉宣纸。
(四)商务印刷馆1932年印行的《商务印书馆精印屏联堂幅价目单附样张》中有“吴愙斋古陶器屏”,所印为吴大澂收藏的四种古陶器的全形拓,列出了尺寸,印制方式、用纸和价格,并配有图样。
吴愙斋古陶器屏,是一套四条屏,全形拓。四尺,金属版,单片价目六吉六角,装裱价目一元三角。
(五)故宫博物院1936年印制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出版物总目》“影印金石”部分列有四种,皆是“文形”拓,即文字拓片,而非器物的全形拓,也给出了印制方式、尺寸和价格。
1、影印散盘(文形),石印,长一点二公尺,宽零点六九公尺,每份六角。
2、影印嘉量(文形),石印,长一点四公尺,宽零点六九公尺,每份六角。
3、影印宗周钟(文形)石印,长一点三二公尺,宽零点六九公尺,每份六角。
4、影印曾伯琦壶(文形)石印,长一点二二公尺,宽零点六九公尺,每份六角。
《总目》“金石拓片”部分也列出了这四种,前两种价格不一样,亦录于兹。
1、影印散盘,已裱者一元四角,文字器形共六角。
2、影印嘉量,已裱者一元四角,文字器形共六角。
其他比较重要的艺术出版机构,如有正书局、文明书局、求古斋等,笔者也搜集到了它们的营业书目,但都没有金石整纸拓复制品的信息,可能是没有此类产品。
笔者还收到了神州国光社1936年印行的《神州国光社书画碑版总目》,遗憾的是书目中并无屏联堂幅的相关内容,结尾有“楹联屏条字幅及印泥等另印细目备索”的字样。笔者虽然多方寻访,依然未找到这份“细目”。所以,神州国光社是否出版过金石整纸拓单片复制品只能暂不讨论。
就营业书目所见资料而言,民国时期金石整纸拓单片复制品以碑拓(包括摩崖和拓片)居多,其次是青铜器铭文拓片,再次为青铜器和陶器的全形拓。砖瓦铭文整纸拓单片复制品仅见于中华书局的营业书目。
金石整纸拓单片复制品的制作方式大致有照相、石印、金属版、珂罗版等,有原大复制的,也有缩印的。
金石整纸拓单片复制品与原拓相比较,具有相当大的价格优势。比如《秦泰山二十九字》,艺苑真赏社的复制品定价八角,1920年,罗振玉公开出售各种新旧拓本,原拓本的标价是五百元。又《秦琅琊台刻石》,艺苑真赏印制的缩本单片,定价四角,罗振玉所售明拓本,标价二百八十元。又《散氏盘》,1935年,西泠印社文字拓本复制品的定价是“洋二元四角(裱工在内)”;1936年,故宫博物院的文字拓复制品定价是六角;而故宫发售的原拓要价是“文字廿五元,器形廿五元。”又《宗周鐘》,1936年,故宫发售文字拓复制品和原拓的定价分别是六角和十元。又《曾伯琦壶》,1936年,故宫发售文字拓复制品和原拓的定价分别是六角和十二元。
营业书目里面的金石整纸拓复制品,有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名字:吴大澂。西泠印社推出的四件复制品,有两件有吴大澂的释文或题跋。中华书局推出的一件复制品,是吴大澂秦汉砖瓦文六条屏。商务印刷馆推出的一件复制品,是吴大澂藏古陶器全形拓四条屏。作为清季重要的金石学家之一,他的藏品和他题跋过的金石整纸拓通过印刷机,化身千万,广为流传。
营业书目资料外的金石整纸拓单片复制品
说起金石整纸拓单片的复制,不能不提顾燮光,他的金佳石好楼整纸原大复制了很多碑志拓片,名为《古刻萃珍》和《古刻余珍》。
郑逸梅说顾燮光“选所藏自汉迄唐精品碑刻三十种,为《古刻萃珍》一、二、三辑,用金属版印行,和原刻不爽累黍,尤为艺林珍赏。”据郑氏所说《古刻萃珍》每辑大约收十种碑刻,但《古刻萃珍》不止三辑,而是至少有五辑,共六十种。顾燮光在写给顾廷龙的信里说:“《古刻萃珍》日内即交邮,全份六函,定价一百元。”又说:“《古刻萃珍》六函计一百元,《古刻余珍》二函计五十元,仍按七折算计一百〇五元,加邮费二包四元六角,共一百〇九元六角。”又说:“燮光昔年用宣纸金属版精印《古刻萃珍》六十种,均系照原式大小影印,下真迹一等。”


《古刻余珍》则有甲、乙、丙、丁四种。顾燮光在写给顾廷龙的信里说:“《古刻余珍》甲种尚存一份,乙、丙、丁尚有。”
《古刻萃珍》和《古刻余珍》的目录笔者迄今未能找到,现综合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六朝墓志检要》《碑帖鉴别常识》和曾克耑《颂橘庐丛稿》所记,并检索孔夫子网的相关交易信息,胪列《古刻萃珍》一至五辑碑志目录如下。
第一辑:汉杜临封冢记、汉鸿都石经表、晋赵府君阙、陈卫和墓志、北魏处士元显隽墓志、北魏曹望憘造像、北魏豫州刺史元珽墓志、北魏尚书左仆射冀州刺史元昭墓志、隋潘城录事参军杨居墓志、隋刘渊墓志等。
第二辑:晋幽州刺史石尠墓志、晋处士石定墓志、隋王氏成公夫人墓志、隋蕲州刺史李则墓志、隋伏波将军典卫令刘相墓志等。
第三辑:北魏侍中太宰武昭王元天穆墓志、北魏鞠彦云墓志、周贺屯植墓志、隋滕王长子杨厉墓志、隋主簿张濬墓志等。
第四辑:北魏尚书左仆射安乐王元诠墓志、北魏元颺墓志、北魏元颺妻王夫人墓志、北魏齐郡王妃常季繁墓志、北魏平州刺史元崇业墓志、隋巩宾墓志等。
第五辑:刘宋刘袭墓志、北魏高植墓志、北魏泾雍二州别驾皇甫驎墓志、北魏豫州刺史乐陵王元彦墓志、东魏刘懿墓志等。
金佳石好楼印行的整纸拓单片还有很多,现亦录名目于兹,以备考索。汉司徒袁敞碑、汉袁安碑、汉君子残石、汉甘陵相尚府君碑、朝候小子碑、毋邱俭丸都山纪功刻石、重庆沙坪䃻九石冈汉墓题字、魏三体石经残石、社正朱阐祀神残碑、晋沛国相张朗碑、晋南阳堵阳韩府君神道残石、晋荀岳暨妻刘简训墓志、晋巴郡察孝骑都尉枳杨阳神道、晋郑舒夫人刘氏残墓志、晋祀后土残碑、晋三临辟雍碑、晋丰县□熊造象、后秦辽东太守吕宪墓表、刘宋刘怀民墓志、刘宋谢涛埋铭、南齐吕超静墓志、南齐刘岱墓志、陈尼慧仙铭、北魏汾州刺史元彬墓志、北魏韩朝宗墓志、北魏前河间王元定墓志、北魏侍中司徒公广陵王元羽墓志、北魏太尉顿丘郡文献公穆亮墓志、北魏城阳怀王元鸾墓志、北魏城阳王元寿妃麹氏墓志、北魏洛州刺史乐安王元绪墓志、北魏江阳王次妃石婉墓志、北魏宁陵公主墓志、北魏王妃李元姜墓志、北魏梁州刺史元演墓志、北魏南梁郡太守司马景和妻孟敬训墓志、北魏冀州刺史元珍墓志、北魏昌国县侯王绍墓志、北魏汶山侯吐谷浑玑墓志、北魏济州刺史长宁穆公杨胤墓志、北魏广平王元怀墓志、北魏雍州刺史刁遵墓志、北魏泾州刺史王元祐墓志、北魏元珽妻穆夫人玉容墓志、北魏城门校尉元腾墓志、北魏平州刺史司马昺墓志、北魏李璧墓志、北魏宫一品太监刘华仁墓志、北魏郑道忠墓志、北魏都官尚书冀州刺史元子直墓志、北魏怀令李超墓志、北魏金城郡君元华光墓志、北魏故处士吴高黎墓志、北魏西阳男高广墓志、北魏银青光禄大夫于纂墓志、北魏胡昭仪墓志、北魏冀州刺史广平王元悌墓志、北魏司空城局参军陆绍墓志、北魏散骑贾瑾墓志、北魏冀州刺史司马穆绍墓志、北魏林虑哀王元文墓志、冯邕妻元氏墓志、刘根造像、北魏东豫州刺史元显魏墓志、东魏南泰州刺史司马升墓志、东魏沧州刺史王僧墓志、东魏兖州刺史张满墓志、东魏宜阳郡王元宝建墓志、东魏渤海太守王偃墓志、东魏伏波将军诸冶令侯海墓志、东魏章武王妃卢贵兰墓志、东魏吴郡王萧正□墓志、北齐太府卿元贤墓志、北齐怀州刺史阳平郡公司马遵业墓志、北齐叱列延庆妻尔朱元静墓志、北齐墨曹参军梁伽耶墓志、北齐颍川太守齐昌镇将乞伏保达墓志、北齐豫州刺史梁子彦墓志、北齐太子太师西阳王徐之才墓志、北齐曹礼暨夫人李氏墓志、北齐扬州长史郑子尚墓志、北周汝北郡中正寇胤哲墓志、隋昌国惠公寇奉叔墓志、隋浮阳郡守王曜墓志、隋车骑秘书郎张景略墓志、隋陶贵墓志、隋刘渊墓志、隋苏孝慈墓志、隋王善来墓志、隋梁瓌墓志、隋孔神通墓志、隋令□堕墓志、隋伍恭公墓志、隋上党郡司功书佐萧㲹墓志、隋始扶汴蔡四州刺史段济墓志、隋通议大夫宋永贵墓志、武周杜山威造像、修通水道记等。
此外,清季的吴云、杨守敬、罗振玉等人都复制过金石整纸拓。
吴云藏有齐侯罍,后来又得苏州曹氏旧藏古罍,遂颜书斋为“两罍轩”。因不断有友人向他索要两罍铭拓本,吴云乃另刻模本以为塞责,这和陈介祺以木刻毛公鼎铭塞责求拓者真真如出一辙。此事见于吴云写给陈介祺的书信中,录于兹:“两罍铭在腹内,极不易拓。曹氏一罍,世间拓本尤少。弟因友人纷纷求索,曾刻有模本,为塞责计。”
杨守敬影印过的金石整纸拓单片比较多,有北魏渔阳太守司马绍墓志、北魏燕州刺史元颺墓志、北魏元颺妻王夫人墓志、北魏齐郡王妃常季繁墓志、北魏银青光禄大夫于纂墓志、东魏沧州刺史王僧墓志、北齐开府参军崔頠墓志、隋邯郸令蔡府君张贵男墓志、隋左武卫大将军吴公李氏女尉富娘墓志、隋太仆卿元公墓志、隋太仆卿元公夫人姬氏墓志等。
罗振玉也复制过金石整纸拓单片。据方若说,光绪二十三年,罗振玉曾取《刘怀民墓志》“原拓脱影百本,以一纸寄来,末行不清。”王壮弘也说《刘怀民墓志》“罗氏另有整纸石印,仅印百份。”罗振玉还影印过《西岳华山庙碑》四明本整纸拓,“用珂罗板照原张大小影印,四边题跋也照样印上。印成后用瓷青细绢裱成大轴,据说与原本样子相同。自有珂罗板影印碑帖以来,这种印法,算是最精采了。”王壮弘说日本也复制过《西岳华山庙碑》四明范氏藏整纸拓,由北京修绠堂发行。因罗振玉常常委托日本人复制珂罗版碑帖,所以未知王壮弘所说的是否就是罗氏印本。
陈介祺的五世孙陈君善,在1930年代取家藏毛公鼎整纸拓石印一百份,用汪六吉棉连纸,拓分三段,上段为鼎铭,中段为释文,下段为器形。
王壮弘说刘鹗曾将《北魏崔敬邕墓志》整纸影印,但笔者查阅诸书,只见有剪裱本,未见整纸拓单片复制品。
复制过金石整纸拓单片的人应该还有很多,囿于见闻,只能罗列这么多了。当有博雅君子补阙查漏,匡我不逮。
金石整纸拓单片复制品的传播与接受:以金佳石好楼影印本为讨论中心
在晚清民国时期,金石整纸拓单片复制品传播的方式大致有三种。其一,通过各个出版机构的发行所和分布在各地的代销书店;其二,通过邮局;其三,亲朋之间互相赠送。
作为晚清民国最为重要的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和商务印刷馆都有很多的分支机构,可以把出版物推送到需要者的手中。西泠印社除了在上海英租界设有总发行所,在全国不少省份和日本都有代销的书店。
除此之外,各个出版机构都开设了邮购业务。在营业书目中,大都有“通信现购简章”、“外埠函购章程”、“邮局代购书籍章程”等等。
顾燮光的金佳石好楼就印行过一种营业书目,名为《金佳石好楼流通金石目录》,所收金石碑拓最早的有秦《峄山石刻》,最晚有隋炀帝大业十二年的《羊山墓志》,《目录》中应该既有原拓,也有复制品。
金石整纸拓单片复制品有着较为广泛的受众群体,他们对这种特殊商品的接受也可以通过考察金佳石好楼的复制品来管窥蠡测。
写过《书学史》的祝嘉有一篇《临书丛谈》,他从学习书法的角度,论及整纸拓的价值。他说:“我们常把碑剪裁,装裱成册,则每个字,只存其上下关系,左右的字,全打乱了。所以碑一经剪裁,就有很大的损失,看不到‘大九宫’了。”他还特别提到顾燮光做的金石整纸拓单片复制品,“影印的本子,也有不加剪裁,依照原拓大小全幅付印的,我所见的有‘金佳石好楼’所印的《古刻萃珍本》,这种印本,价廉物美,是很好的,可惜不见再印了。”
曾任国史馆纂修、新亚书院教授的曾克耑有《五十年来影印碑帖谈》和《真行草墨迹及石刻影印述略》,也对顾燮光影印的金石整纸拓单片表彰再三。他说:“再谈一位爱好碑帖的顾老先生燮光。他是会稽人,一生喜欢在荒山野水之间,访求古刻,中年在河南,访碑九年,访得未著录的碑刻不少,一面访碑,一面将新出的各项碑志造象残石等类,以整幅原大四字为原则,影印以供同好把玩,影印有几十种,现在市面上已不多见,将来可能变成希贵之品。”在论及《杜临封冢记》的时候,他说:“会稽顾鼎梅博学好古,收集古今石刻,照原式大小影印,总名是古刻萃珍。此记是其中之一,书体俊逸,得此影本,无异于得见原石拓本,传印古刻,莫妙于此。”在论及《袁敞残碑》的时候,他说:“会稽顾鼎梅照照原石大小影印,拓本流传不多,有此影本,同好者可无向隅之叹。”在论及《熹平石经周易残字》的时候,他说:“会稽顾鼎梅得初出土未断裂时拓本,照式影印,与拓本相比较,丝毫未变。此种拓本,原本不多,原拓既不可得,获此影本,亦可见此石未断裂时状态。”在论及《朝侯小子碑》、《刘熊碑》、《修通水道记》、《重庆沙坪䃻九石冈汉墓题字》、《袁安碑》、《毋邱俭丸都纪功刻石残字》、《三体石经》、《赵府君阙》、《祀后土残碑》、《三临辟雍碑》、《石尠石定墓碣》、《刘怀民墓志》《晋丰县□熊造象》、《齐郡王妃常季繁墓志》、《元颺夫妇墓志》、《鞠彦云墓志》、《刘懿墓志》、《元诠墓志》、《元显魏墓志》、《刘根造象记》、《高植墓志》、《元显隽墓志》、《元天穆墓志》、《皇甫驎墓志》、《武周杜山威造象记》等的时候,曾克耑不吝笔墨,一再揄扬顾氏刊印的整纸拓单片复制品。
鲁迅在1917年5月16日的日记里,也提到顾燮光赠以影印整纸拓单片。“顾鼎梅送《琬琰新录》一本,石印《元显魏墓志》一枚,季市交来。”此外,顾氏复制的金石整纸拓单片,有一件《吕超墓志》,是鲁迅题过跋的。据许寿棠《亡友鲁迅印象记》所记:“我知道吕超墓志石出土以后,经年即为舍亲顾鼎梅所得,藏在杭州,舍亲范鼎卿及鲁迅均有跋文,考证详明,两人不谋而合。鼎梅曾将这两篇跋文付石印,因即驰书商索,承其寄示,不禁狂喜。”
潘伯鹰在《中国书法简论》中列举了一些学习书法的范本,其中《汉君子残石》、《魏刘根造象》就推荐了“金佳石好楼影整片”,而《毛公鼎》和《散氏盘》则推荐了“艺苑真赏社单印片子”。
周煦良也特别认同顾燮光的金石整纸拓单片复制品,他说:“像民国初年顾鼎梅金佳石好楼石印的那些整张石刻,纸不过连史,墨不过少些油气,然而已经很可以供欣赏了。”
启功《论书绝句》,咏“朝侯小子碑”诗自注中,也说此碑拓曾为顾燮光辑入《古刻萃珍》。可见启功也见过金佳石好楼的整纸拓单片复制品。
通读上述各家评品,我们不难发现金石整纸拓单片复制品的接受者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习字者,他们把整纸拓当成学习书法的好范本,因为整纸拓有助于他们了解并学习古代书法作品的章法。艺苑真赏社的复制品,大都是针对这一群体制作的。第二类是欣赏者,在他们眼里,整纸拓和名人书画一样,可供观赏,也可以装点居室。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西泠印社都把整纸拓单片复制品归于屏联堂幅类,而且经常裱成立轴或条屏出售,应该是针对此类消费者群体的。其三是研究者,如鲁迅、曾克耑等人,更多的是把整纸拓当成研究的对象,或据以考据经史,或据以研究书学。金佳石好楼影印的金石整纸拓单片似乎在三类接受者中都有市场,而这三类接受者也不是泾渭分明的,他们的身份也可以重叠,既可以是习字者,又可以是欣赏者和研究者。
余论
整纸拓在相当程度上再现了金石的原貌和全貌,这一点是剪裱本难以比拟的。不少金石遗迹历经岁月,早已湮没无存,它们的整纸拓和整纸拓复制品在金石学研究中就更加不可或缺。比如《古刻萃珍》第四辑所收魏元颺墓志、魏元颺妻王夫人墓志、齐郡王妃常季繁墓志,“为宣统二年在河南洛阳同时出土,为碑贾郭玉堂所得。后售与武进董康诵芬室,未几董氏即售与日本,藏太仓集古馆中。一九二四年(日历大正二年)九月一日,日本大地震,此三志与《晋张朗碑》等与馆俱毁。今《张朗碑》已重加修复。此三志惟《王夫人志》尚以铁束紧缚残损不多,余二志皆已碎成数小块。”

整纸拓单片复制品的大量出现体现的是印刷技术的进步。摄影术和印刷术传人中国,不仅在书籍印刷上得到广泛应用,也在艺术品复制上一展拳脚。以往那些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因为印刷技术的进步,被大量复制。朱自清回忆他初到清华大学的时候,去拜访教务长张仲述,“张先生客厅里挂着一副有正书局印的邓完白隶书长联。我有一个会写字的同学,他喜欢邓完白,他也有这一副对联;所以我这时如见故人一般。”朱自清在张仲述家和同学家都看到过的这幅对联见于有正书局的营业书目,联语是“桐荫清閟云林阁,鸿雨烟沉海岳盦”,定价是六角。邓石如作品真迹是什么价格?民国九年,罗振玉发售金石书画,目录中有“邓石如篆书立轴(纸本)”,标价是二百五十元。书画如此,拓片亦然,很多珍稀的碑志拓片也借助印刷术化身千万,走进寻常百姓家。
整纸拓单片复制品的流行也体现了新的观看习惯。以往普通人看碑志拓片,看到的大都是剪裱本。晚清民国时期,出现了新式的艺术展览会,整纸拓比剪裱本更适合各种展览。1926年,河南被灾,潢川书画收藏家吴宝炜发起“河南筹振金石书画展览”,征集到的展品中有很多金石整纸拓,如《初拓爨龙颜碑整幅》、《初拓爨宝子碑整幅》等。也是1926年,10月4日,鲁迅写信给许广平,也提到以整纸拓参加展览会的事,他说:“……不日要开展览会,除学校自买之泥人而外,还要将我的石刻拓片挂出。其实这些古董,此地人那里会懂,无非胡里胡涂,忙碌一番而已。”《鲁迅日记》也不乏装裱拓片的记录,如1917年8月24日有记:“下午往琉璃厂取所表拓本,凡三十枚,付工四元。”同年11月18日有记:“……又至敦古谊取所表拓片三十枚,工五元。”据邓云乡说当时碑帖铺的伙友,都要学会裱拓片。“因为拓片不论白纸、黄纸,纸质都很薄,翻弄的次数多了,很容易弄破,一定要把它裱一下:一种裱法是把拓片一条条地剪开来,装裱成册页式或长卷式;一种只是用东昌纸或皮纸衬一下,就是不把拓片剪开,只是在拓片背面再裱一张较坚韧的衬纸。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常记裱拓片的事,都是指后一种。……(鲁迅)日记中这类记载还很多。每张裱工合一角四、五分。鲁迅先生所以如此裱拓片,并不是因为这样裱便宜,主要是这样裱可以保存碑的原样,录碑时便于按尺寸、行数、字数观察研究,考校原文。如果剪开来,裱成册页或长卷,考校起来,就不大方便了。”承接晚清金石学的流风余绪,再加上1919年以来的“整理国故”之风的鼓荡,研究和展览一样,不仅影响了人们对金石拓片的观看方式,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石拓片的装裱和保存方式。因为研究和观赏的需要,金石整纸拓单片复制品也更加盛行。